时间:2016-06-02 点击:3825
西方医学的麻醉正式始于1846年,在此之前的麻醉可以说是用草药和鸦片做止痛来减轻外科的痛苦。麻醉在台湾的发展也是如此,大致上以日据时代和台湾光复的年代来分为三个大阶段,分别是荷兰人据台至清末日本接收台湾、日据时代和台湾光复后至今。台湾由于天津条约之故,于1859年开放门户,西方医学才得以进入,而西方医学的传入也同时开启了麻醉这一神奇又多采多姿的一页。
十六世纪之时,荷兰占领南台湾时,就极力从事殖民工作,西方人除殖民之外,来台的动力即在传教和医疗。明朝天启5年(1625年),占领台南安平时的省长Dr. Marten Sonk即为西医师。另据长崎商馆日志记载,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因母和妻染恶疾,于1640年延请荷兰外科医师Philips Hijlman由台湾至厦门去诊治,滞留三个月才返台。在那个时代,外科医师兼作麻醉,如何做并不知道,但可确信的是教士和军医随荷军、东印度公司和西班牙军队入台,早有外科的医疗行为。
在明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人据有北部基隆时,道明会神父Fn. Bartolome Martinez就随着12艘中国戎克船和二艘西班牙战舰与五名教士登陆,并在和平岛建立教堂,隔年Francisco Mola神父又带了四位教士在附近扩展建立教堂。由于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和修士,很多是具西医知识的人员,因而传教和医疗是合并进行的。据巴达维亚城日记的记载,1637年4月,日本长崎代官平藏有封致荷兰总督的信中就有感谢他由台湾转至日本的医师Maerten Wesselingh的治病和造酒的欣喜。另外1641年12月,东印度公司有自安平离开的船在广南遇海难,其中82人遇救,被虐几致死,只有砲手二人,外科医师一人反而被广南王任用,足见当时医疗之珍贵。当时荷人在台湾已设有西医院,「1645年1月……,派阿多里亚……勒尔调任孤儿财产管理所长兼医院管理人,……载至台湾窝湾(安平)之药箱不整齐,一如证明书短少多数药品。」(巴达维亚城日记(二), 450-451页,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而西医院的地址为安平区延平街86号,今为安平文化资产馆。于1661年郑荷之战时(巴达维亚城日记),「司令官Jacob Caeuw……于8月12日……安全抵达大园锚地,……该舰队之前来,于Zeelandia城引起异常狂喜,甚至病患及跛者亦跳出病房,欢声四扬。……」「本事件之后,经检阅我兵员,发现健全旧兵370人,新兵498人在城与堡垒之内。病患300人则在医院。由于此次不幸战斗,长官及评议会决定嗣后对敌人不再出于攻势,以防战为主。」拜咸丰九年天津条约之便,台湾门户开放,西方人通商和传教,也将西医和麻醉的神奇带入台湾。1859年道明会神父郭德刚(Ferdinando Sainz)自福建厦门至打狗登陆,于1861年建立万金(屏东)天主堂,1864年建立鼓山天主堂时,随行的修士即已做些医疗的宣教行为,但麻醉的医疗并未提及。
1864年,英长老教会派了首任医疗宣教士马雅各(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M.A.,M.D.)来台医疗传道,并于1865年6月16日设立了今日新楼医院的前身-看西街医馆,马雅各医师在台南执行切除白内障和肾结石手术,成功治疗不少病人,但其麻醉方式并没有详述。另外在1872年加拿大长老会派马偕牧师(Dr. George L. Mackay)于淡水的传教事业中,亦建立了今日的马偕医院。由于长老教会原来即以医疗传道的主要方式来台,所以相关的医疗资料比较多。例如在彰化,1895年抵台的兰大卫(Dr. David Landsborough),正好接上日据时期,以他为主在彰基的医疗事业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根据清代「海关医报」记载,住淡水医员Dr. B.S. Ringer于1875年与加拿大长老教会医疗宣教士华雅各Dr. Jacob B. Fraser共同切除头颈部肿瘤,其中记载:「病例1 - KIAM是一位56岁女性病患……4月26日,病人在麻醉剂的作用下,切除肿瘤,皮肤边缘以银线缝合……之后病人回家,并带着一些抹疼痛的锌药膏,一星期后,她自己又回来……」;「病例2 - KHIN,一位56岁的苦力,1875年12月9日来诊所……,我们给予病人一剂量的鸦片,因为他没用麻醉剂忍受手术……」,以上可能为目前台湾最早纪录使用麻醉剂和术后止痛的文献。
另外,根据「海关医报」,驻台南的海关医员W. Wykeham Myers(英皇家外科硕士)于1879年7月上任,于其服务期间为一位动脉瘤的病人做了气管切开术,此例为台湾最早的呼吸道重症处置的治疗纪录:「……病人濒临窒息,幸运的是同事安彼得医师(英长老会宣教士)的帮助……我们在甲状腺的峡部上打开气管……」(见中央大学历史研究论文---清末洋人在台医疗史,苏芳玉着)刘铭传曾于1884年10月19日亲自到淡水马偕医馆,向主治医师约周漠森与英舰克苦合法号军医布罗恩医师致谢他们于法军封锁台湾期间,对战伤士兵的治疗照顾,并捐款给医院(台湾的过去与现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但对于其中手术治疗并未说明麻醉细节。由于现代麻醉学的发展始于1846年,在军队里和早期的在台传教人员中有部分的手术已使用了西方的医术和麻醉方法,有些记载必须从教会人员的历史纪录中去寻求。光绪12年,刘铭传设立了台北官医局,特召西人医师驻任,亦为有感于西医神奇之效。
这时期以彰基为例,其医院在1919年左右,平均一个手术日的早上有12台刀,其中有两三个大手术。(见于「兰医师Dr. Lan」连玛玉着,刘秀芬译)除此之外,兰医师每日要看400个以上的门诊病人,可见西医当时在台湾受到相当的重视,而麻醉的情形是由兰医师做半身麻醉,再由护士把脉(由王光胆医师提供)。大约1910年,兰医师训练的医员中,高年级的学生必须负责麻醉的帮助。「1920年,麻醉使用Chlorform倒在纱布上由此渗入,病人闻药约10分钟就麻倒了。麻醉中若病人移动或快醒,就再滴几滴麻醉药。麻醉中的监视仅靠观察病人瞳孔的变化,若瞳孔变大,即不再加药,否则会麻太深。……」(麻醉科简史 王锦华、蔡铭雄)。
当时有一份由中国医疗传道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于1887年3月开始发行的杂志──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兰医师于1913年9月联合小马雅各医生在这刊物提出一篇文章 『A PROTEST AND A CHALLENGE』,表达其对于Dr. Samuel Cochran发表在同一期刊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中关于氯仿的使用建议上的异议。在Dr. Cochran的文章中认为氯仿的危险是不容置疑,因为「……休克现在已经知道很大的因素是因血管收缩的神经轻度瘫痪,氯仿对血压有很深的压制作用,病患用这种药物会很快显现出休克的症状。尤其在急诊外伤的病人是一种禁忌,虽然它方便于使用时的决定,可是病人容易处于休克现象……」,在其引用的学者研究中显示氯仿对于有脂肪变性的心脏病人造成肝小叶中央坏死现象,有时会造成身体剧烈的不适而致命,而在对狗的实验上,一天使用2至3次,将会使狗死亡。此外亦会造成血液循环上凝血的问题和孕妇的致命。Dr. Cochran亦指出在美国当时已出现对于氯仿的使用采取反对的态度。
然而兰医师和小马雅各医师对于氯仿的应用与Dr. Cochran大为不同,在他们的论文中提到,认为Dr. Cochran的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因为他们的经验是,在他们的医院(台南医馆和彰化医馆)中,使用氯仿麻醉的手术中造成的死亡,在10,000件中,仅有5件(这5件分别是两位有巨大卵巢肿瘤的患者,均在手术开始前死亡、一位是下颚坏死、一位是有水胸的分娩病例、一位是外国人气管碰撞的病例)。而这5位都是因为在手术前已出现呼吸障碍,因此算起来,他们因氯仿造成的死亡率是1/2000,且施行麻醉者由一些受过训练的中国助手来做,并非由受专业训练的麻醉人员。而他们运用在所有的手术中,包含一般的及特殊的外科手术,如几百例的下腹部手术,许多甲状腺切除、脓疡症等病例,并未见到在氯仿麻醉后中毒的。他们更强调这并非表示氯仿对中国人的危险性低于英国人或美国人,这也许是医师未注意酒精,或者全然未注意到使用氯仿后的中毒是因饮食中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手术前没有空腹所致。他们并劝告那些对这个问题抱持着犹豫的外科医师同业们,直到有明确的证据提出前,不要放弃目前所拥有且提供良好的、可靠的麻醉技术。这篇论文和Samuel Cochran的『RECENT ADVANCES IN ANESTHESIA』,把麻醉在台湾的情形做了一个最早期的描述。
对于当时运用麻醉的经验和态度上,兰医师与文辅道(Dr. Harold Mumford)合著的文中(1972年)提到:「不只小型的手术,连许多大型的手术都使用局部麻醉(注射Cocaine preparations),而不少于全身麻醉(吸入Chlorform或Ether),这证明局部麻醉是很舒服的,且病人宁愿在手术时能保持清醒而免于疼痛。这对于经常处于危急状态中的急性下腹部病症者尤为重要。我们有信心将对于许多嵌闭性疝气的病患能够免于氯仿的致命性归功于局部麻醉。」当时连拔牙也全身麻醉,台湾民众对于麻醉的观点是有点害怕,但有过麻醉经验的病人却觉得免痛很了不起,并称麻醉为「迷be」。
1928 切肤之爱转载自彰化基督教医院
《兰大卫医生与百年医疗宣教史》
于1928年开创台湾医疗史上器官移植的先例──皮肤移植的切肤之爱也说明了麻醉的部分角色,「……此次手术乃为异体移植,参与的医师有兰医师、苏振辉医师、许琨医师。手术过程为以氯仿为周童(周金耀牧师)和兰医师太太进行全身麻醉,先为周童清除……」(辅仁大学历史所论文---台湾医疗传道史之研究 赖志中着),故事主角周金耀回忆说:「在手术期间,由于麻醉药力不够,我于麻醉中甦醒,亲见兰医师正对他太太动手术……」(彰基百年纪念麻醉科简史 /王锦华、蔡铭雄)因有个不完美的麻醉,造成了动人完美的历史见证。

1928 切膚之愛轉載自彰化基督教醫院《蘭大衛醫生與百年醫療宣教史》
当时在麻醉和西医的教学方面,教材大多由日本取得,而彰 化教会另行训练医学生所使用的书是由宣教士以白话罗马字自编的(以厦门音为主)教材,修业年限为四年,毕业证书是由日本总督府颁给的岛内医生免许状,授课老师为兰医师、林朝干、林一鹿、林安生等人。授课在晚上,学生白天为服务病人,高年级生负责麻醉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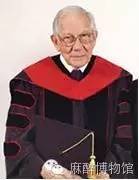
2004年兰大弼医师
接受台南神学院
『荣誉人文博士』学位

兰大卫医师(三世)
入爱丁堡大学时留影
根据本编辑小组访问目前退休在英国的兰大弼医师(Dr. David Landsborugh)──小兰医师是兰大卫医师之长子,是台湾神经科医师的先辈,他禀承父志,曾于福建泉州惠世医院(今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前身)从事医疗传道工作,大陆沦陷后来台并扩充父亲创始的彰基成为当时台湾中部最大的西医院。关于日据时代的麻醉情形,他有如下的说明(口述):「基本上,我父亲对于全身麻醉是比较习惯的,因为他本人是爱丁堡医学院所训练的人,你知道Chlorform的发源地就是爱丁堡大学,这种麻醉方法与日本人和台北毕业的医学生的认知是有些不同,当时日本人医生和台北毕业的医生对于全身麻醉是有点怕怕的,他们可能对于半身麻醉反而相当重视,甚至有些只做局部麻醉。……至于麻醉训练是和一般的医学训练一起的,教材有从德国、日本和英国来的,日本人这一点很有意思,陆军学德国,海军学英国,医学两者都学。 我父亲在彰化训练的医学生平均是四至五年,然后参加考试及格,日本政府颁给证书,可以准许在乡下开业,他们都有学麻醉,大约两至三年,父亲对于他们有信心了,则可自行开刀麻醉的作业,这大概是1925年至1930年左右的事了。……我记得我十四、五岁时,我到大陆读书(编者按,至大陆烟台读书,每年回台一次),有次放假回来进开刀房,看我父亲手术,那天早上有一台是盲肠炎,有一台是脓胸手术,上全身麻醉;接着又看见一位许医师,是台北医学校毕业的,也做了三、四个手术。……另外是有关于术后的止痛,你知道当时伦敦大学使用Morphine是很普遍不过的事,手术前会给一些,手术后也给。我父亲也有这么去做,但日本时代,他们很注意这个药,怕上瘾,所以很小心地给,给很少,台北毕业的医生也是对这个药很小心,这是很敏感的事情。(编者按,日据时期约1900年代,吸鸦片人口有160,000人,约全台6.3%的人口,约1942年的小兰医师的时代,全台吸鸦片人口已减至6000人,是因为改为严禁政策之故。)当然手术后加护照顾那个时候就不像台北马偕或台南新楼,我父亲一向认为愈简单的是愈好的……。」
清末中国的积弱实始于一种麻醉药剂──鸦片,鸦片战争失利后,列强趁虚而入,中国门户大开,日本深知鸦片之危害,故于其本土实施严禁政策,但在台湾这块「土人」之殖民地,基于殖民考量和财政的利益,却是采取放任的态度,即渐禁政策,但却绝对禁止将鸦片传给日人。当时其众议院副议长岛田三郎的话:「支那人种一般嗜吸鸦片,台湾土人亦承其弊,传病毒于子孙……鸦片断需解禁……,然而,剥夺其多年积习之嗜好,是土人最难忍受之事;更进一步可藉由此事,若有违反者,直接捕拿驱逐出境。如此,直接可得鸦片禁止之利益,间接则有支那人种驱逐之利益,这岂非一举两得?」(1895年9月5日,「太阳」---谢春木着「台湾人的要求」pg.159-161),而在台的有志之士,如:蒋渭水、蔡培火、韩石泉等人有感于此,在组织「台湾民众党」时公布的诉求中,第二条即为反对鸦片的许可政策,甚至于民国17年致电日内瓦的国联,请求阻止这个政策,是年制定了日内瓦国际鸦片协定。
由于国际上的压力和鸦片利益的减少,日本政府才开始在台实施被国人视为「耻辱」的鸦片许可政策改为严禁,并且由当时台湾第一位留日医学博士杜聪明先生来组织和实施,成立了更生院,以杜氏为院长,做戒瘾的行动,当时的内务警察课就有鸦片取缔部门,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受鸦片危害之烈。杜博士在1931年至1945年间与其团队就鸦片问题就发表了21篇论文,这也是台湾在麻醉学术研究上最早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篇是世界最早由尿中吗啡含量来诊断鸦片上瘾的文献。另值得一提的是,杜氏也研究蛇毒中神经毒素的分离,该制剂类似麻醉药品可治疼痛且无成瘾副作用,似可取代鸦片。以后台大医学院的药理研究所在他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扩充,对其他医学领域亦提供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帮助。